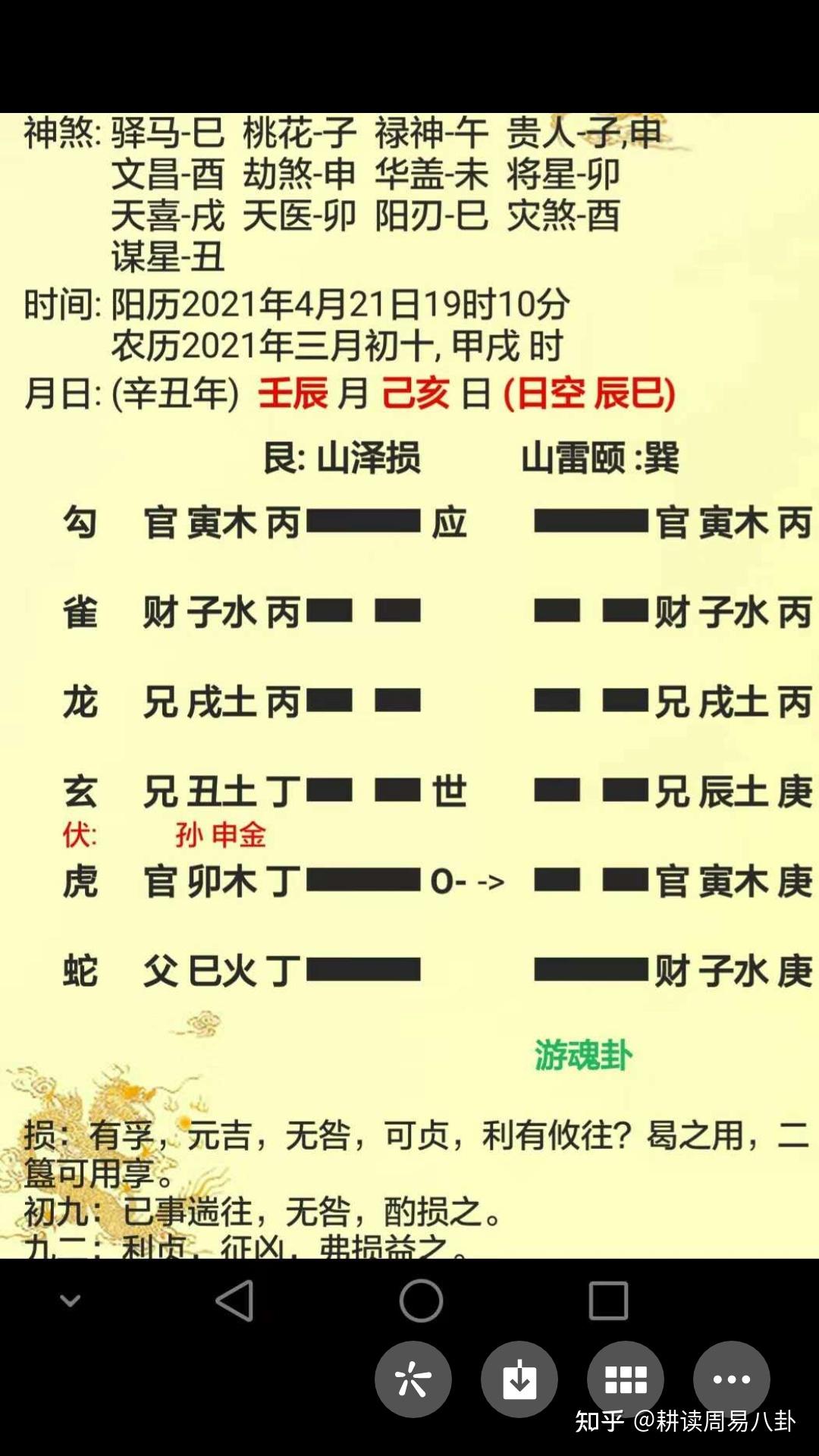摘要: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周易义疏和周易集注,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关键词:《论语》;“仁”;诠释;体用一源
体用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朱子思想里占有重要地位。朱熹对体用颇为关注,也最善言体用,“几乎到了泛滥的地步”,但其运用范围很难界定。陈荣捷立足其言语文字规律,总结出朱熹言体用具有体用有别、体用不离、体用一源、自有体用、体用无定、同体异用六种原则,但总体认为“朱子未尝著一有统系之体用论”。朱熹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和丰富了体用一源思想,这一思想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学者甚至称其为“程朱理学的宗旨和核心”。朱熹不但把体用及体用一源思想运用于本体论,而且进一步用以说明心性情和伦理道德。“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是贯穿始终的讨论伦理道德之主线。朱熹对“仁”的体用诠释颇具特色和思想理论价值。张栻在与朱熹反复讨论“仁”之后,称道朱熹以“爱之理”言“仁”亲切可见,并由此结合未发已发、仁之体用等总结出“体用一源,内外一 致,此 仁之 所 以妙也。”可见,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系统考察朱熹对《论语》“仁”的诠释不啻为一个值得切入和深入研究的问题,而这还不曾有人进行专题研究。为此,本文拟在梳理朱熹体用一源思想的基础上,立足其体用一源“非一物”之核心观点,分别从体用有别、体用一源两个角度,探讨朱熹是如何既强调仁为体又强调仁兼体用的,并进一步分析其在朱熹理学建构中的作用及其背后的儒学立场。
一体用一源“非一物”:
朱熹对体用一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朱熹体用一源思想是对周敦颐及二程的继承、批判和发扬。他高度评价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包含“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其《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载
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
在这里,朱熹认为,周敦颐思想高远幽深处有“无极太极之妙”“阴阳五行之赜”,但不离“日用”,不离“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实用,其中贯通有秦汉以来未曾有过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思想。
首先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是程颐《易传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是就如何把握《周易》中义理和易象之关系而提出这一原理的。他认为,义理是隐微无形的,易象是表现义理之显著外在形象,两者融合无间;义理是隐微之本体、易象是显在之作用,两者一致而同出一源。后来,程颐又把用以阐释《周易》的这一体用思想进一步加以推广,将“体用一源”引向到“事理一致”,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于易学上的意义普及到天下的理、事关系,并且强调,“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
对此,朱熹有继承,亦有发展、有侧重。他于1172年43岁时在《答何叔京》一文中有过明确表达:
“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观,则理为体、象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显微无间”者,自象而观,则象为显、理为微,而象中有理,是无间也。先生后答语意甚明,子细消详,便见归着。且既曰有理而后有象,则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与无间耳。其实体用显微之分则不能无也。今曰理象一物,不必分别,恐陷于近日含糊之弊,不可不察。
上述引文明确表达了两层思想:一是理中有象,象中有理,体用一源而无间;二是先有理而后有象,理、象非一物,体用有先后之分,体用显微之分别“不能无”,否则就会陷于“含糊之弊”。对于第一层意思,朱熹两年后,即1174年45岁时在《答吕子约》一文中也有表述,对于吕子约“体用一源而不可析”之体用合二为一观,该文称赞“此说甚善”。
对于第二层意思,朱熹强调,伊川既说“有理而后有象”,便表明理象有先后、体用有先后,不是一物。其实,朱熹早在1170年41岁修订成《太极图说解》时,即言: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着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
朱熹认为程颐“体用一源”的说法其实非常缜密。“体用一源”是从理这一方面说,理为体,事象为用,理中就有象,先体而后用;“显微无间”是从事象这一方面说,事象为显,理为微,事中又有理,先显而后微。体用两相比较,体为先为精,用为后为粗,二者有粗精先后之别。同年,朱熹在《答吕伯恭问龟山中庸》一文中亦就伊川原话论议:
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体,达道言其用。体用自殊,安得不为二乎?”学者须是于未发已发之际识得一分明,然后可以言体用一源处。然亦只是一源耳,体用之不同,则故自若也。
“大本言其体,达道言其用,体用自殊,安得不为二乎”,是伊川解释《中庸》之语,意在以体用范畴规定“大本”与“达道”之关系。伊川还曾说:“大本言其体,达道言其用,乌得混而一之乎。”在此,朱熹引用伊川原话,旨在进一步论证和说明,体用本来是不同的两种东西,只有“识得一分明”,然后才能讨论体用一源,“体用之不同”是体用一源之前提。对此,朱熹还于1197年68岁时在《答吕子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至于形而上下,却有分别。须分得此是体、彼是用,方说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说得无间。若只是一物,却不须更说一源、无间也。”在这封回信中,朱熹从正反两面阐述强调,要分清体与用、象与理是有分别的此和彼,唯有如此,才能谈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从上面的书信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不论早年还是中晚年皆关注体用一源之体用分别和联系。在朱熹看来,体和用、理和象“同源”“无间”,理中有象,象中有体,但理象并非一物,体用有分别,体和用可合而为一,更应分而为二。朱熹在肯定体用“一源与无间”的同时,特别强调体用之分。“然体用自殊,不可不辨。”朱熹认为,体用之别、体用不只是“一物”,是说“一源”“无间”的前提。这是朱熹体用一源思想的核心要义,也是其侧重点,更是其分别以体用诠释“仁”的理学基石。较之程颐,朱熹对“体用一源”的思想内涵论述得更为全面和细致,而这亦是周敦颐等前儒不曾涉及的。正如陈荣捷所言:“朱子之言体用,大体沿程子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然朱子范围之广,分析之详,远出于程子之上,亦为后儒之所未及者。”
二分别体用释仁:朱熹强调仁是体
朱熹用体用一源思想释仁,基于对体用分别之强调,明确提出了仁是性、是未发,性是体,未发是体,仁是体;爱是情、是已发,情是用、已发是用,爱是用。在区分仁与爱、性与情、未发与已发、体与用的同时,朱熹强调:“仁之得名,只专在未发上。恻隐便是已发,却是相对言之。”仁是体,仁的得名专在未发之性、体上,与爱的得名相对而言。
其一,朱子认为,性是未发、情是已发。1172年,朱熹《答何叔京十八》曰:“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若不以未发已发分之,则何者为性,何者为情耶?”此处明确指出,性情的分别只在未发已发的不同,应该用“未发已发”来分辨“性情”。其《太极说》一文进一步指出:“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在朱熹看来,性情的未发已发是就性和情的相互关系而言,性是“情之未发者”,情是“性之已发者”,“未发”为性,“已发”为情。
其二,朱子认为,仁是性、爱是情。《朱子语类》载:
“仁者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犹言生之性,爱则是理之见于用者也。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爱是情,情则发于用。性者指其未发,故曰“仁者爱之理”。情即已发,故曰“爱者仁之用”。
在这里,朱子通过解释“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用”透彻揭示了仁与爱两者之间的关系。仁是爱之理,是未发之性;爱是仁之用,是已发之情。1172年,朱熹与张栻论“仁”第一书《答张敬夫(论仁说)》对此有进一步讨论:
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及其发见,则仁者恻隐,义者羞恶,礼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体以见其本,所谓“情也,性之发也”。……却于已发见处方下“爱”字,则是但知已发之为爱,而不知未发之爱之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与义、礼、智均为发见,则是但知仁之为性,而不知义、礼、智之亦为性也。
朱熹于此处提出,根于心的仁义礼智四德是未发的“性之德”,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端是已发的可见本的“性之发”、是爱。换言之,从“未发”的角度看,仁与义礼智一样,是“性之德”,是性,是“未发之爱”;从“已发”的角度看,“不忍之心”即“恻隐之心”、爱,不同于未发之仁、义、礼、智等“性之德”,是情,是性之发。
其三,朱子认为,仁是未发、爱是已发。《朱子语类》载:“仁之得名,只专在未发上。恻隐便是已发,却是相对言之”;“恻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未发,爱是已发”;“爱是恻隐,恻隐是情,其理则谓之仁。”在朱熹看来,仁之所以叫做仁,就在它有“未发”之意,孔子答司马牛问仁曾说“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篇);同时,仁是未发,爱(恻隐、情)是已发,两者是相对而言的。朱熹还用互为未发已发的性情关系对应诠释仁爱互为未发已发的关系,以此分别仁和爱。《朱子语类》载:“须知所谓‘心之德’者,即程先生谷种之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程颐谷种之说为:“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可见,朱熹从未发之性的角度视仁为“心之德”。而正如性是情之未发、情是性之已发一样,朱熹释仁为未发之爱,释爱为已发之仁,借“(性情)未发已发”道出了仁、爱互为未发已发之关系,两者区别自然显而易见。
其四,朱子认为,仁是体、爱是用。1190年,朱熹于《答方宾王》一文中说:“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可见,仁是性、是体;恻隐(爱)是情、是用,仁爱有别。《朱子语类》载:“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则是情。恻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体,爱是 用。”在这里,朱熹也明确指出,仁是性、是体,恻隐是情、是爱、是用,由性、情推导出仁是体、爱是用。朱熹在《孟子或问》中强调:“恻隐亲亲固仁之发,而仁则恻隐亲亲之未发者也。未发者,其体也,已发者,其用也。”此处,朱熹由未发、已发推导出仁是体、爱是用。朱熹用体用之分突出性情之别和仁爱之别。1172年,朱熹于《答张钦夫(论仁说)》中言:
下章又云:“若专以爱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遗其体,言其情而略其性,则其察之亦不审矣。”盖所谓爱之理者,是乃指其体性而言,且见性情、体用各有所主而不相离之妙,与所谓遗体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请更详之。
朱熹此处从正反两面进行阐释,就正面而言,仁被释为“爱之理”,性情、体用有“不相离之妙”,是“指其体性而言”;就反面而言,性情、体用各有所主,仁爱有别,不可“以爱命仁”,否则就是指用而遗体、言情而略性了。显而易见,朱熹在这里是强调仁爱、性情、体用之分别的。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诠释仁,不忘点出仁、爱(恻隐)之同,但着墨更多的是仁、爱之别。正如其1173年给吕祖谦书中所说:《仁说》“其实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爱情之说,但剔得名义稍分,界分脉络有条理,免得学者枉费心神,胡乱揣摩,唤东作西尔”。仁是性、是未发、是体,不同于爱是情、是已发、是用。那么,在朱熹看来,仁爱、性情、未发已发、体用这四对关系之间有何关联呢?陈来先生强调,“朱熹对未发已发的使用更多用以指性与情之间的体用关系”;“性情未发已发则是与体用相同的概念,两者不但在实际上有过程的区别,层次也不相同”。中和新说后,朱熹认为未发、已发之不同体现出性、情之体、用的不同。因而,在《孟子或问》中,朱熹强调,仁是未发之体,爱(恻隐)是已发之用。朱熹总体认为,仁与爱(恻隐)、性与情、未发与已发同体与用是对等的概念,两两各自分属不同层次,仁、性属体的层面,爱、情属用的层面。就其发用具体而言,静而伏藏于内者宜属体,动而发用在外者宜属用;性静而伏藏在内,故属体,情动而发用于外,故属用;仁者爱之理,伏藏在内,属体,爱(恻隐)则动而发用在外,属用。
三体用一源释仁:朱熹强调仁兼体用
朱熹继承和发展程子体用一源思想,一方面主张体用“非一物”、有分别,并以此释仁,强调仁是体;另一方面,主张体用“同源”“无间”,可以合二为一,以此释仁就突出强调仁兼体用。对于后者,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
其一,朱子认为,仁之体用不相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中本来就包含体用有则具有、不相分离之意,朱熹反复申明了这一点:“然体用自殊,不可不辨,但当识其所谓一源者耳”;“体用是两物而不相离,故可以言一源”;“要之,体用未尝相离”。他在诠释仁之体用特征时更是予以明确阐述。《答何叔京十八》曰:“仁无不统,故恻隐无不通,此正体用不相离之妙。若仁无不统而恻隐有不通,则体大用小,体圆用偏矣。”朱熹认为,体用大小圆扁相配,此正仁之体用具有“不相离之妙”,体用不离之仁无所不统包,当它表现为用之恻隐时,就是无所不贯通。《答张钦夫(论仁说)》载: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爱,情也。岂可便以爱为仁?”此正谓不可认情为性耳,非谓仁之性不发于爱之情,而爱之情不本于仁之性也。熹前说以爱之发对爱之理而言,正分别性、情之异处,其意最为精密。……盖所谓爱之理者,是乃指其体性而言,且见性情、体用各有所主而不相离之妙。
在这里,朱熹认可程子区分仁性爱情的观点,但并不因此而割裂仁与爱、性与情、体与用的关联,认为它们虽然“各有所主”,应区别对待,但更应看到性发于情、情本于性,性情、体用具有“不相离之妙”。
在讨论“樊迟问仁”章时,朱子对仁之体用不相离有更为明确的表述。《朱子语类》载:
文振说“樊迟问仁,曰‘爱人’”一节。先生曰:“爱人、知人,是仁、知之用。圣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迟,却不告之以仁、知之体?”文振云:“圣人说用,则体在其中。”曰:“固是。盖寻这用,便可以知其体,盖用即是体中流出也。”
或问:“爱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体告之?乃独举其用以为说。莫是仁知之体难言,而樊迟未足以当之,姑举其用,使自思其体?”曰:“‘体’与‘用’虽是二字,本未尝相离,用即体之所以流行。”
在上述两则对话中,朱熹明确指出,仁之体用“未尝相离”,寻用便可以知体,用是从体中流出的。
其二,朱子认为,全德之仁无不统。1172年,朱熹《克斋记》言:
性情之德无所不备,而一言足以尽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盖亦多术,而一言足以举其要,曰“克己复礼”而已。盖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是以未发之前,四德著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已发之际,四端著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
在这里,朱熹明确指出,仁备性情之德,“无不统”,具有全德之义。具体而言,可概括为四层意涵。一是从“(性情)未发已发”来看,仁包括未发的“性之德”,又包括已发的“情之德”,同时具备“性情之德”,是全德。二是从“情之未发,性也”的角度看,朱熹言“未发之前,四德具焉,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统”,释“仁、义、礼、智”为性,为“四德”,为“性之德”,强调仁这一“性之德”统“仁、义、礼、智”四德,“仁包四德”,是全德。三是从“性之已发者,情也”的角度看,朱熹言“已发之际,四端着焉,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而恻隐之心无所不通”,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情、为“四端”,强调“恻隐之心”这一“仁之端”通“四端”,“恻隐之心包四端”,是全德。四是从体用之总体特征看,仁之体用具有“涵育浑全、周流贯彻”的特点,能“专一心之妙、为众善之长”。
1172年,朱熹在撰写《克斋记》后,又作《仁说》。《仁说》曰:
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周易义疏和周易集注,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
在此,朱熹反复论述仁“无所不备”、兼具体用的特征。一是以“心之德”言仁,仁具有“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的特征,自然兼体用。二是与天地心有四德相类比,人心也有四德四用,“仁无不包”,恻隐之心“无所不贯”,仁包四德,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不待遍举而该”,仁兼体用。三是仁为“生物之心”“爱人利物之心”,未发时是体,已发时是用,“包四德”(强调仁之性和体),“贯四端”(强调仁之情和用),仁自然“体无不在”“用无不行”。
其三,朱子认为,专言之仁兼体用。《朱子语类》载:“以‘心之德’而专言之,则未发是体,已发是用。以‘爱之理’而偏言之,则仁便是体,恻隐是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是朱熹对《论语》“为仁之本”之“仁”的诠释。“心之德”释义同于孟子言心“兼体、用”、“该贯体用”,是兼未发之体、已发之用来释仁,是专言;“爱之理”释义,突出仁是体、爱(恻隐)是用,同于程子言“仁是性,恻隐是情”,“分体用而对言之”,是分别体用而言,是偏言。
对于“克己复礼为仁”之仁的诠释,朱子亦有类似表述。“如‘克己复礼为仁’,却是专言”。朱熹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之仁是专言之仁。“专言仁者,是兼体用而言”,“仁对义、礼、智言之,则为体;专言之,则兼体、用”。在朱熹看来,专言之仁,自有其体用,兼体用。朱熹弟子直卿亦如此说:“若独说仁,则义、礼、智皆在其中,自兼体用言之。”很显然,直卿的观点是与老师观点一脉相承的。
朱熹1196年67岁时《答欧阳希逊》曰:
大率孔子只是说个为仁工夫,至孟子方解仁字之义理。(如“仁之端”在“仁,人心”之类。)然仁字又兼两义,非一言之可尽,故孔子教人亦有两路,(“克己”即孟子“仁,人心”之说,“爱人”即孟子“恻隐”之说。)而程子《易传》亦有专言偏言之说。如熹训释,又是孟子、程子义疏。可更详之。
在这,朱熹指出,从孔子、孟子到程子,仁字兼有两义,孔子之仁兼“克己复礼为仁”之“仁”和“爱人”之“仁”两义;孟子之仁兼“仁,人心”和“恻隐之心,仁之端”两义;程子之仁兼专言之仁和偏言之仁两义;他自己释仁兼“心之德”和“爱之理”两义。而在朱熹看来,孔子之仁虽兼两义,但他说的只是为仁工夫,到了孟子才算真正解释了仁字的义理。因此,朱熹强调自己承接的是孟子、程子的义疏。实际上在具体文本解释时,朱熹强调以“爱之理”释仁近于孔子的“仁者,爱人”、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程子的偏言之仁;以“心之德”释仁同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之仁、孟子的“仁,人心”之释、程子的专言之仁。“心之德”是专言之仁,包“爱之理”这一偏言之仁,兼体用。
性情不离,心统性情;体用不离,仁兼体用。体用不离是朱子释仁兼体用的前提。朱子既强调“心之德”是全德,是性情之德,统兼体用;又承程子专言、偏言之说,界分“心之德”“克己复礼为仁”等所释之“仁”是专言之仁,强调专言之仁兼体用。
四结语:体用释仁的儒学立场与现实关怀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朱熹分别以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仁的得名专在未发之性、体上,与爱的得名相对而言。这其中有严谨的逻辑理路: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同时,朱熹以体用一源、合体用释仁,强调仁兼体用,以“专言”“心之德”释仁,突出专言之仁兼体用,心之德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统包仁、义、礼、智四德,贯通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仁之体用涵育浑全,周流贯彻,未尝相离。朱熹于1172年43岁时承继、综合孟子和程子仁的义疏,在《仁说》中以“心之德”“爱之理”说仁,在1177年其48岁成书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明确以“心之德”“爱之理”定义仁:“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一方面,从体用不同的视角,释仁为“爱之理”,突出仁为性、体,为偏言,不同于为情、为用之爱;另一方面,从体用一源、合体用的视角,释仁为“心之德”,突出仁兼四德之体用,为专言,是性情之德,是“全体大用”之仁。朱熹以体用一源释仁,贯通未发已发、心统性情、形上形下等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孟子、周敦颐、程子等前人的思想,促进了理学建构的发展和完善。
在西方和印度哲学中,普遍流行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本体、现象截然两分的观点;释、老二氏惯于割裂体、用关系,倡导“体用殊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家重视义理、否定象数,主张“得意忘象”;等等。陈来先生指出,程颐“体用一源”思想的提出,是对张载批判二氏“体用殊绝”、倡导体用不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朱熹继承程子等人观点,丰富并发展体用一源思想,既强调体用不同,又突出体用不离,圆融而全面,并将其贯彻于对仁的诠释之中,既驳斥了二氏的“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
作者简介:郭园兰,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