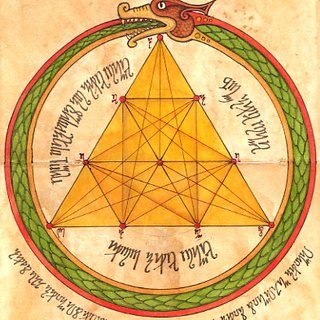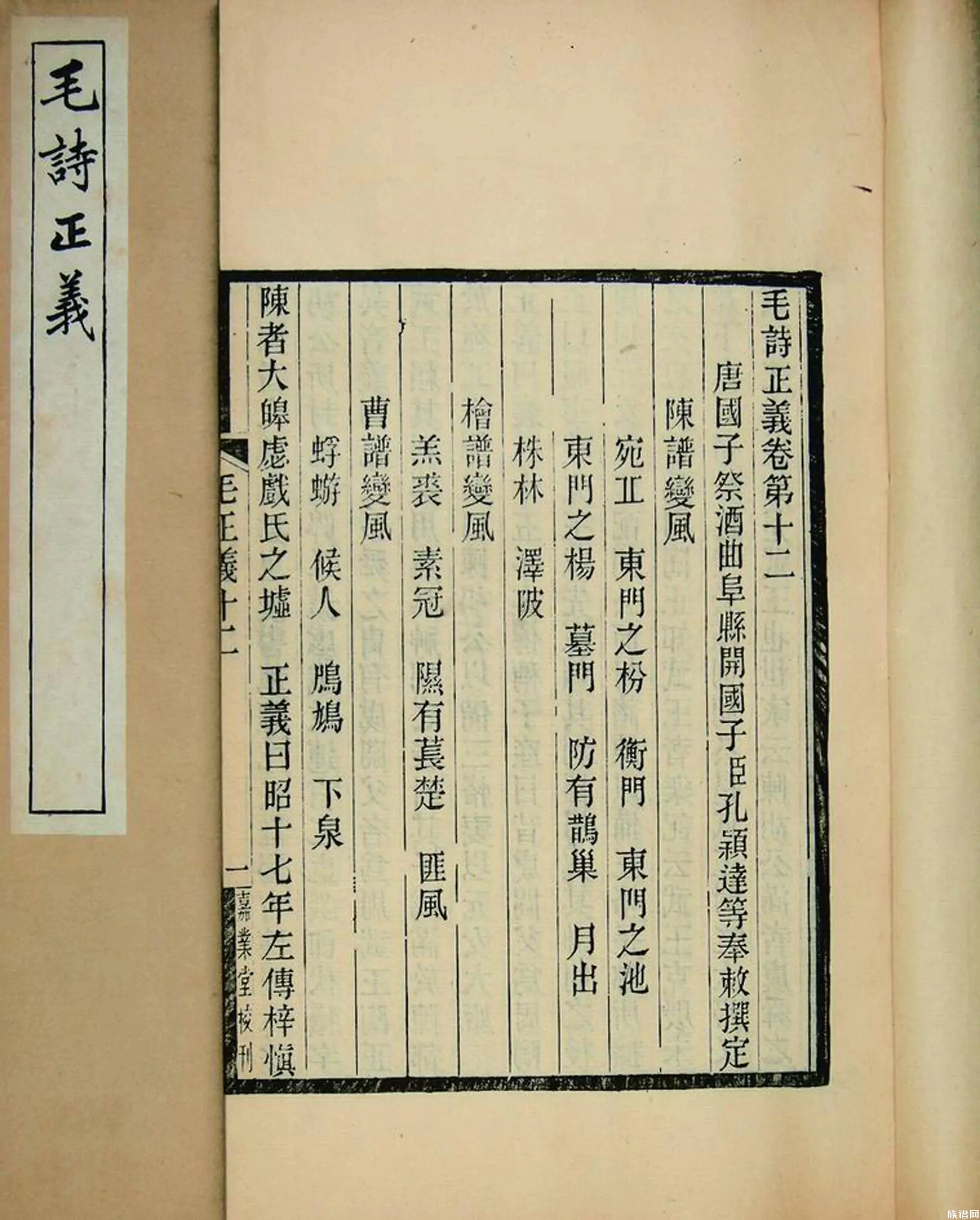文献学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且我国文献学自古以来就有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因此在文献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果远不如文献整理领域那样丰富。自春秋末年孔子提出“文献”一词,后世学者对“文献”的涵义作出的种种阐释,实已开启文献学理论研究。而西汉成帝时期,以刘向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对国家藏书进行的系统整理,开创的广罗异本、确定书名、审定篇章、校勘文字、缮写定本、撰写叙录、类分图书等一套严密的文献整理程序与方法,已孕育了丰富的文献学思想与方法,班固《汉书·艺文志》用“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尚不能完全概括之。前文阐述的“文献观”是古代文献学理论的基石,而从典藏、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传注、编纂等文献整理活动中归纳出来的经验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则构成了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这个体系如同古典文献学(即校雠学)的学科体系一样,是一个松散的结构,且是完全本土化的。
典藏学理论与方法
对文献实体的保存性整理活动规律的归纳总结,即形成文献典藏理论。文献典藏理论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国家藏书事业的认识。如宋代的程俱还在《麟台故事》中阐述了他对国家藏书事业的认识,认为国家藏书乃“典籍之府,宪章所由”,事关国家的治理。该书还全面阐述了北宋藏书机构的历史沿革、行政隶属、功能价值、建筑设计、藏书机构的社会文化意义等。第二,对文献聚散规律的认识。如元初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1]清代曹溶在《流通古书约》中谈到宋以来文献典籍的散佚情况:“自宋以来,书目十有余种,粲然可观。按实求之,其书十不存四五。”[2]李清照在谈到赵明诚的藏书时也经常感叹:“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3]这些藏书理论都带有辩证色彩。学者们还对文献典籍散佚的原因进行分析,如隋代的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总结了历史上文献五次大的劫难,称之为“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在此基础上又增至为“十厄”。第三,对藏书流通与管理的认识。如清代已有一些私人藏书家开始提出图书共读和流通的思想。如曹溶《流通古书约》对私家藏书提出了“有无相易”、“互抄互换”等倡议,以便文献的流通和共享。李如一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蕴涵了“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的理想,并允许普通图书外借。第四,对藏书家流派的总结。如明代胡应麟将藏书家分为两类:“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觸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沉湎青箱,却扫闭关,蠹鱼岁月,鉴赏家类也。”[4]。清代学者洪亮吉受其启发,将私人藏书家归为考订、校雠、收藏、赏鉴、掠贩五类。近代学者叶德辉将藏书家又分为著述、校勘、收藏、赏鉴四类。
至于文献的采访、赏鉴、装潢、管理等方法就更加丰富。举其要者,如在文献采访领域,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提出了著名的“求书八法”(即类以求、旁类以求、因地以求、因家以求、求之公、求之私、因人以求、因代以求),至今有借鉴意义;在文献赏鉴方面,明代藏书家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的《藏书训略》中对如何收集、鉴别文献阐述了自己的心得。祁氏认为,购书时“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鉴别文献时要“审轻重”、“辨真伪”、“核明实”、“别品类”。这些带有经验性质的理论与方法的总结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
版本学理论与方法
版本学理论主要是指在鉴定版本和考订版本源流活动中形成的“善本观”,它是指导前人研究版本的核心理论。所谓善本观,是指在版本鉴别和选择过程中,于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图书版本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一种综合价值取向。历史地考察善本观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善本的概念是由“善书”和“本”的概念发展融合而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版本观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如汉人在今古文之争的社会背景下崇尚正本和古本;魏晋以来对佛经的翻译和整理使得对原书正本的需求,成了这一时期的当务之急;南北朝时,一方面由于纸张的广泛应用,书籍的生产呈活跃的状态,版本数量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政权更迭,战事频繁,公私藏书聚散无常,加上书籍在传抄过程中的眼讹手误,误本迭出。因此,这一时期文字内容没有错误或少有错误的精校本便成了人们的追求;隋唐人继承了崇尚前朝旧本的传统,但对文献的装帧和外观形式有了更高的要求。至两宋时期,人们的善本观已发展成熟,表现为崇古本、旧本、写本;尊官本;嗜金石拓本;重精校本;求足本、完本。同时,对版本的外在形式也有了更高的审美追求。在具体的文献环境下,宋人的善本观还呈现出灵活变通的特点,如针对尚古风气发展到极致,陆游提出善本不必是古本旧本;针对历代重视官本的传统,朱熹提出善本当以“文势义理”为准,“无论官私”;重视精校本,并不是提倡以己意妄改文献的内容,彭叔夏提出善本当为不“轻以意改书”者;得真本、正本固然可喜,但如果不能尽得,也可退而求其次,吴若提出善本“虽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为异者”等观点。明清以后,善本观的发展更趋成熟,并呈现不同的学术流派。另外,在单书版本源流考订方面,东晋僧人在对佛经翻译整理过程中,最早提出“万流同归,百虑一致”[5]的思想,这与今人版本源流考订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版本学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版本鉴定和版本源流考订两个方面。鉴定文献版本的目的是从现有存本中发现善本,其途径不外乎两大类:一是通过文献版本的外在形式,二是通过文献版本的文字内容。可以为鉴定文献版本提供线索的外在形式有书名页、序跋、卷端、牌记、行款、字体、刻工姓名、装订方式、纸张、藏印、室名等,通过对这些外在形式上标记的版本信息进行比较,去除因为重刻、翻刻甚至剜改、作伪留下的错误的版本信息,准确地辨析出文献的真实出版地、出版者和出版时间;从文字内容入手鉴定文献版本的具体途径,包括图书的卷数、编例、内容时限、名物制度、学术源流及讳字等方面,主要是从以上信息源留下的时代特征来比较分析文献的真实出版地、出版者和出版时间。当然,在文献版本鉴定实践中,往往是通过以上两种途径,综合运用多种鉴定方法,经过比较后从中择出出版年代最晚的线索来作出判断。
版本源流有两重涵义:一是指文献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大体属出版史研究的范畴,本文不作探讨;二是指单书版本的演变源流,也就是单种文献(含丛书)首次出版之后的历代版本传承、变化情况。考察单书版本演变源流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单种文献各个版本在历史上的传承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存本中哪个版本更接近祖本,从而为文献整理获得优良的底本。其方法大致如下:第一,通过考察作者传记、祖本序言、相关书目题跋及进书表等,分析出文献的祖本面貌,比如书名、卷数等关键信息;第二,通过遍查历代书目、相关序跋及现存馆藏书目等,查考祖本之后的历代同书异本的情况;第三,通过对历代同书异本的版本信息的比较以及内容的分析,辨析各个版本之间的孰前孰后以及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从中找出与祖本关系最为亲密的存本。
目录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以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为第一个高峰。与一般目录学家强调提要不同,郑樵主张通过科学的文献分类方法,使学者“睹书而知义”,“学术自明”。他在阐述文献分类的意义时说:“善为学者,如持军治狱,若无部伍之法,何以得书之纪,若无核实之法,何以得书之情?”所谓部伍之法,就是以“类例”的方式使得学术体系自现;所谓核实之法,就是将这种理论与文献分类的实践结合起来。“类例”即分类体系。郑樵提出“编次必谨类例”,认为“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不明,图书失纪”,“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因此,“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6]。
明代胡应麟的《经籍会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经籍会通》以历代书目为纲,分源流、类例、遗轶、见闻四篇,对目录的作用、发展、体例、类型及文献分类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如对于目录的作用,他认为:“往代之书,存没非此无可考;今代之书,多寡非此无以征。”[7]也就是说,通过书目既可考历代文献的存佚情况,也可知今代文献的多寡聚散情况。入清以后,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读书治学经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目录学的功用,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中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8]
清人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代表了中国目录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高峰,其核心思想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在《校雠通义·自叙》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阮元刻周易正义,千百之中不十一焉。”[9]所谓“辨章学术”,就是将纷繁复杂的学术脉络条分缕析,使之彰显;“考镜源流”,就是撮取古今学术发展的史料,通过鉴别比较,溯其源流正变。具体来讲,就是通过文献分类、著录(包括互著、别裁)、类序、解题等目录学方法,将各家学术流派的学者、著述及学术发展源流梳理得井然有序,达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目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成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理论的核心思想。
目录学在揭示和报道文献的内容与形式特征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居特色的方法体系,包括著录、解题、分类、文摘、索引、书评、综述等。此不一一赘述。
校勘学理论与方法
我国校勘学自汉代到清代,名家辈出。汉代为校勘学的开创时期,代表人物有对西汉国家藏书进行系统整理的刘向、刘歆父子,其后有遍校群经的郑玄、校释《淮南子》等书的高诱;隋唐至元明时期为校勘学的发展时期,代表性成果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颜师古的《汉书注》和《匡谬正俗》、朱熹的《昌黎先生集考异》、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辩证》,以及刘绩的《管子补注》等;清代为校勘学的全盛时期,形成了以惠栋、钱大昕、顾广圻等为代表的吴派校勘风格,以及以戴震、卢文弨、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俞樾、孙怡让等为代表的皖派校勘风格。
校勘理论主要在于阐释校勘的目的和功用,总结校勘方法。凡校勘者,均以恢复文献祖本的旧貌为目的,如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同时对《汉书》进行了必要的校勘,提出要通过“曲核古本”,消弭后世之人任意刊改增删《汉书》造成的错讹,达到“归其真正”,“克复其旧”的目的。但在恢复祖本原貌的路径上,清代两大校勘学派在理念上发生了分歧。以卢文弨、顾广圻为代表的吴派学者主张对不同版本之间的异文予以保留,反对臆断擅改,提出“以不校校之”的理论;而以戴震、段玉裁为代表的皖派学者认为,应该用文献考据的方法对异文进行取舍,勇于改字,提出了“以贾还贾,以孔还孔”的著名观点。两者在校勘理念上形成了所谓“死校”与“活校”的差异,前者关注的是为后人提供集合了不同异文的底本,后者在意的是为后人提供内容准确无误的定本。
因此,在校勘方法上,也形成了所谓的“死校法”和“活校法”两大流派。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形成的是集合了各种异文的底本。活校者阮元刻周易正义,“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择善而从,版归一式”[10],得到的是确认无误的定本。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他个人对《元典章》校勘的实践经验,又归纳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四种方法,成为文献校勘的经典方法。
辨伪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伪书的产生可追溯到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而疑古辨伪的工作也始于此,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宋时期风气大盛,而明清时期更是拓宽了文献辨伪的范围,在辨伪思想和方法上有了许多创新。特别是在清代,辨伪与考据的结合,涌现出胡渭、崔述、姚际恒、阎若璩、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等一大批辨伪学家。
早在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在《淮南子·修务训》中,分析了“尊古而贱今”是伪书产生的主要原因。东汉的马融发现诸书所引《尚书·泰誓》之文皆不见于传本《泰誓》,从而认定传本《泰誓》是伪作,首创据佚文证伪的方法。南朝的刘勰发明了文体辨伪法,对当时流行的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进行考辨,认为大多可疑。北齐的颜之推,则擅长从名物典制及史实的角度进行辨伪,指出不少典籍如《尔雅》、《春秋》、《世本》、《苍颉篇》、《列仙传》、《列女传》等有相互矛盾之处,证明其中有后人附益的成分。
最早对辨伪方法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的是明代的胡应麟。他在《四部正讹》中提出了八种辨伪方法: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以上八种辨伪方法涉及书目著录、文献征引、文献体裁、社会背景、作者托名、流传经过等方面,非常全面,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梁启超在其所撰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里,总结出了十二条辨伪公例,总结起来就是利用目录学知识辨伪、利用逻辑常识辨伪、利用文体和语言常识辨伪、利用学术史知识辨伪、从伪书所依据的材料上辨伪、利用反证的方法辨伪。梁任公又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里对考证伪书的方法有更为详细的概括和总结,比胡应麟的“辨伪八法”系统和精密得多。今人对文献辨伪,所用的方法也不外乎这些。
辑佚学理论与方法
古代书目、伪书、杂钞等文献的形成过程中,经常伴随有辑佚活动。如《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所谓的“捃摭遗逸”就带有辑佚性质;东晋梅赜所献伪《古文尚书》,很多篇句都能找到出处,可见它不是凭空架阁,而是采缀古书而成;唐代马总的《意林》,是从各种类书、经注中,将当时已经亡佚的汉朝以前诸子著作中的散见条文摘抄出来,杂编成书。
但辑佚作为一门学问的形成,大概是在宋代,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郑樵在理论上提出了文献“名虽亡而实不亡”的观点:“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俱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俱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明代胡应麟在辑佚理论方面也有一定贡献,他关于对古佚书的考辨、对佚文的搜集整理、对时人辑佚现象的总结、类书在辑佚中的作用以及辨伪法在辑佚中的应用等问题都有重要阐述,代表了明代辑佚理论的发展水平。
至清代,辑佚学已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理论,涌现出章宗源、严可均、王谟、汪文台、黄奭等一批辑佚学者,并明确提出了辑佚为“学”的概念。民国以来,辑佚学理论有较大发展,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辟“辑佚书”一节,总结评述了辑佚的历史,指出“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列举了辑佚“所凭借之重要资料”,提出了四条“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另外,梁氏在其专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辑佚产生的原因、辑佚的起源、辑佚的价值和意义等也多有论述。
与版本鉴定、校勘和辨伪不同,辑佚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文献整理工作,其工作内容不仅融合了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的方法,还要借助目录学、史源学、注释学(传注学)、编纂学等文献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并有相对严格和复杂的工作程序,包括佚书的认定、佚文的搜集、佚文的加工、佚书的编排等。
注释学理论与方法
注释学又称训诂学。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对文献的注释作品,如《春秋》的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和《易传》等。从汉代开始,不同名称、不同方式、不同风格的文献注释作品大量涌现,两千多年来,注释发展成为我国文献整理和文献生成的重要方式之一。从注释名称来看,有传、集传、注、集注、解、集解、笺注、训、诂、训诂、说、章句、音义、疏义、正义、直解等;从注释对象来看,有文字注释、语法注释、修辞注释、内容注释等;从注释类型来看,有辨字、注音、释义的区别,释义又有以形说义、因声求义、随文释义等不同方法。注释学与传统的经学关系密切。可以说,经学的发展、衰微与复兴,无不是以注释经典为其标志。清人经学著作,仅阮元于道光年间编选的名著就有180多种,名曰《皇清经解》;王先谦于光绪年间辑乾嘉以后经学名著和乾嘉之前的阮元《皇清经解》漏收者又209种,名曰《续皇清经解》。两书共收经学注释作品390余种,共计2830卷。这些著作都以经典的语言、义理和条例为研究对象,从广义上说,全都是注释学著作。
对文献注释理论具有奠基性质的是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原则。从文献生成方式来看,注释是“编述”的一种重要方式。“述”在《说文解字》里释为“循也”,对于文献注释而言,就是要求注释者必须遵从原文,不得擅自改易或发挥,以致偏离作者原义。但在我国文献注释史上,还是发生过“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论争。所谓“我注六经”,就是以训诂的方法理解文献的本义,达到对先贤本真思想的把握。从方法上讲,即就经作注,经注相贯,重视文献考据,发挥微言大义是其末节;所谓“六经注我”,则是借注释经典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方法上多用义理之法,文献考据是其末节。清代学者戴震对注释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东原文集》里对训诂的功用、训诂的前提、训诂的对象、从事训诂的条件、训诂方法等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继之而其的是今人黄侃。他在《训诂学讲词》的“训诂述略”中,详列训诂之意义、训诂之方式、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义训与声训、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以声韵求训诂之根源、求训诂之次序、声训、声训分类等,使清代之前的注释实践上升为一门有体系的理论学科,从而彻底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
编纂学理论与方法
编纂是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之上对文献内容进行编述和抄纂的总称。编述是“将过去已有的书籍,重新用新的体例,加以改造、组织的工夫,编为适应于客观需要的本子”,而抄纂是“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11]。前者是用编者自己的语言复述、裁剪和融合原有文献的内容,不予保留原文;后者是对既有文献的照抄(又分全录、节录、摘录等不同方式),保留了原文字样。在中国文献史上,大多数经书和几乎全部史书都是编述的产物,如经书基本上是以原始的“五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为基础,加以注释、阐发和引申;史书都是在原始的起居注、实录等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加以裁剪、熔铸和钩玄。另外,佛经的翻译及西方文献的翻译也都是编述的结果。抄纂的文献类型则有类书、丛书、杂钞、档案类编及部分文集等。
因为编纂涉及与既有文献的关系,所以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自然成为指导文献编纂的理论准则,即文献编纂必须尊重历史和作者原意。而在具体文献编纂实践中,中国古代学者也创作性地总结出一系列理论与方法。如西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阐述编纂《史记》的动机,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通晓古今历史发展变革的规律。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其中大量涉及史书体例、编纂方法等内容。如他第一次对史书与史料进行了区分:“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12]刘知几还就选材提出了“博采”和“善择”的观点,阐明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按照先编“丛目”,次编“长编”,最后删削定稿的程序,将史料抄纂与史书编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后世史书的编纂开创了“通鉴体”。南宋的郑樵正式提出了文献编纂中的“会通”理论。他在《上宰相书》中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13]“会”就是汇聚天下之书,为此他发明了“求书八法”;“通”则有“纵通”和“旁通”两说。“纵通”是依据事物的发展演进而对史料进行时间上的先后联缀和贯通,达到“极古今之变”的目的;“横通”则是依据事物的空间展开而对史料进行扩充和推演,达到“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通志·总序》)的目的。换句话说,“会通”的基本学术思想是“视天下书为一书”,将百家学术视为可以融会贯通的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是对司马迁文献编纂思想的新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从“道器合一”的角度阐述了文献编纂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并在刘知几区分史料与史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史书划分为“著述”与“比类”两大类,提出了“比次之书欲其愚”的文献编纂原则。所谓“比次之书欲其愚”,就是要求文献编纂者不要自作聪明,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忠于文献原文。这是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总叙[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清)曹溶.流通古书约[M]//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5.
[3](宋)赵明诚.金石录[M].济南:齐鲁书社,2009:257.
[4](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6.
[5](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5:310.
[6](宋)郑樵.通志·校雠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书社,1990:721.
[7](明)胡应麟.经籍会通·卷3[M]//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8.
[8](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
[9](清)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叙[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1.
[10](清)叶德辉著;李庆西标校.叶德辉书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0-11.
[11]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7.
[12](唐)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31.
[13] 郑樵撰;吴怀祺校补.郑樵文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