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次访谈结束时您提到您认可成中英先生“《周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活水”的说法,并指出“从《周易》出发梳理中国哲学的起源是没有问题的”。这次您可否具体谈一下《周易》与中国哲学的起源问题?
杨庆中:成先生把《周易》视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活水,与他对伏羲时代文化发展的考察及哲学分析有关。我还没有成先生的认知高度,我之所以认为“从《周易》出发梳理中国哲学的起源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夏商周三代皆有《易》类典籍,此类典籍均掌于帝王和巫史之手。上次我曾引用已故著名经学家、史学家金景芳先生的观点,指出三代的巫史实际拥有当时没有分化的全部科学知识。所以透过巫史所掌之《易》,我们能大致洞悉三代、特别是周初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而他们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也正是先秦诸子进一步思考宇宙、社会、人生的起点或基础。
其次,《周易》的功用在于沟通神人(天人),是神人(天人)之学。通神是巫史的本分,而通神有着古老的传统,如《尚书?吕刑》、《国语?楚语》等典籍中均曾记有“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的故事,就与巫史通神有关。《易传》追溯伏羲作八卦,不但把伏羲描绘成了史官的形象(“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还把他作八卦的目的归结为“以通神明之德易经就是中方哲学嘛,以类万物之情”,即沟通神人(天人)。沟通神人(天人)一直是巫史的工作,直到汉代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实际上仍是指这种沟通的工作,“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对于史官的核心功能和主要任务的高度概括。《周易》掌于巫史之手,是巫史通神的经验总结,也是巫史通神的教科书或参考答案,《周易》也因此而成为神人、天人之学。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关系问题实滥觞于此。
第三,《周易》沟通神人(天人),目的在于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寻找根据。上次我提到了《尚书?洪范》中的“稽疑”。“稽疑”就是决疑断惑。《洪范》“稽疑”条指出,天子有“大疑”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即自己的看法,卿士、庶人的看法,以及卜与筮的结果。这几者之中,卜筮占其二。虽然占其二,但却很关键,所谓“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意思是说卜与筮结果不吉的话是要宁静勿动的。因为卜筮均不吉乃意味着帝王的某一决策或某一行为没有得到神灵的支持,因而没有合理性。所以卜筮实际上隐含了为天子——人存的世界之存在方式的合理性和合理存在的可能性寻找根据的意涵,这也正是天人问题的核心意涵。
第四,上次我们提到了中国哲学的起源与忧患意识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有一个说法:“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因此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哲学源于好奇。这固然不错,但中国哲学的产生,还有其特殊的向度,即对三代政治及宗教的反思,反思的核心是天命何以转移的问题。周初统治者基于对该问题的深刻反省,不断发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和“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告。这就是所谓的“忧患意识”。周人的这种忧患意识与文王有关,《易传》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综合这两段材料,可知文王作《易》乃是出于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周公那里表现为“以德配天”命题的提出。此一命题的深层哲学意涵仍然关乎神人、天人等问题。因此也可以说,中国哲学源于周初统治者与知识界对三代天命转移的“诧异”。
总之,《周易》作为一部凝聚夏商周三代知识分子——巫史集团智慧的著作,它对宇宙存在形式的理解,对神人关系的把握,对人之行为合理性的探索,以及它所蕴含的强烈的忧患意识等等,为先秦诸子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基础,为先秦哲人的哲学思考留下了丰富的解释空间,对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周易》出发梳理中国哲学的起源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刚才的说法很有启发意义,您提到了“源头活水”中的“源头”,这个“源头”是如何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础并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重大影响的?或者换句话说,《周易》之作为“活水”的意义是如何体现的呢?

杨庆中:您的问题很犀利,我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谈。首先,《周易》内涵一个基本结构,即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是一个包含了卦时、爻位和卦时、爻位对应的吉凶——人的结构系统。限于访谈的体例,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证,我只是大略说一下。在这个系统中,卦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爻位服从于卦时,而人则要服从于爻位和卦时。这个结构系统其实就是符号化了的天地人的整体宇宙论系统,天地人,《易传》谓之“三才”,汉代学者把三才与六爻的爻位结合起来,认为初爻二爻为地,三爻四爻为人,五爻上爻为天。这种理解是否合理是值得研究的。就《周易》而言,卦时-爻位-人之吉凶的结构,或者说天地人的结构是最根本的,这种结构构成了一个人在宇宙中寻求合理位置(吉凶休咎)的符号化演绎系统。因此《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探究的都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每一卦探讨的都是人在宇宙中如何积极地寻求自己的合理位置并因此获得存在的合理性的问题。这一点后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宇宙论的原始形态和基本结构,因此对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次,《周易》有文字即卦爻辞,有符号,即卦爻象,卦爻辞是用来解释卦爻象的。卦爻辞规定性强,卦爻象抽象性高,二者之间的张力为人们留下了诸多理解的空间。例如,辞因象而立,每卦每爻所系之辞有确定的内涵,也以追求准确地解释卦爻象为其目标,这反映了古人对概念之确定性的追求(尤其是后来的象数易学)。但概念的确定性也是其局限性,有局限就无法全面完整地反映卦爻象的意涵。而在《周易》中,卦爻辞的确定性并没有遮蔽掉卦爻象的超越性,可以说象辞的巧妙结合为辞的确定性和象的超越性都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并最终让二者都指向一个基于宇宙整体性的人之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易学史上解易体例之所以能够不断出新,易学家们之所以能够透过新的解易体例融会新知,讲出一套新的哲学,即与《周易》象辞关系的此一特点有关。
另外,《周易》象辞关系的这一结构也引申出了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等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就是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言”指卦爻辞,“象”指卦爻象,“意”指卦爻象要表达的本质意义。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有趣,“言”是语言、言说、表达。而“象”虽然具体所指是卦爻象,但《周易》的卦爻象所“像”的是宇宙万物。所以象辞关系实际上指的是言词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意”则是指宇宙万物的法则。这三重关系是孔子率先揭示出来的,孔子认为“言不尽意”,也就是说“言”无法圆融地表达“意”。怎么办?“圣人立象以尽意”,圣人透过“象”来完整地呈现“意”。在这里,古人用卦象象征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然后透过对卦象的认识来认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所以,《周易》的每一卦就是一个宇宙图示,冯友兰先生受朱熹的启发,谓之“宇宙代数学”。我觉得可以谓之动态的宇宙图示或模型,只要你在这个图示或模型中能定位到此时此地的你,就能获知你当前的处境所具有的吉凶之意。这是不是一种比较有特色的知识论进路?大家可以研究。另外孔子的“言不尽意”说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说,两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也很值得思考。
第三,《周易》作为一部筮占之书,重视对神意、天意的考察,但六十四卦之中又处处彰显着吉凶由人的精神,这一矛盾留下的解释空间很大。《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一卦每一爻都在讲吉凶,但占者是吉是凶,端赖自己的选择。例如《乾》初九“潜龙,勿用”,大意是说(《乾》卦初九这样的情境暗示的是)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下不宜有所行动。但行动还是不行动则完全取决于人之自身,因而吉凶取决于人的选择。又如《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大意是说(在《坤》卦六四这个情景里),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说话可以避免灾祸,当然也不会获得荣誉。但管得住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还是取决于人之自身,而吉凶取决于人的选择。《周易》的这种吉凶由人观,彰显了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张力,从哲学的视角说,是自由与必然之关系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但人们鲜少提及的自然与人文、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此外,八卦、六十四卦符号本身具有的超出文字的表达功能,《易传》解经过程中运用的一些概念范畴等,都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乃至于科技史上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上次谈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进入《周易》,都离不开对《周易》经传的研究,因为易学史上的很多问题都是从《周易》经传中引发出来的,《易传》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解释《周易》的著作,那么,孔子是不是《易传》的作者?
杨庆中:《易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部诠释《易经》的传世文献,史载该《传》出于孔子之手。但宋代以后,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怀疑。不过,终整个经学时代,孔子作《易传》的观念,始终是易学研究中的主流看法。近代以来,由于思想观念和学术方法的变革,有些学者,比如古史辨派的学者致力于“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孔子之作《易传》的传统观念,自然也就成了怀疑的焦点。不过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完全肯定《易传》为孔子所作和彻底否定孔子与《易传》有关,均没有十分充足的证据。《易传》各篇未必成书于一时,但大致是在春秋末至战国末这一时期。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传》可知,历史上关于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孔子不但“晚而喜易”,还曾跟弟子们讲授《周易》,可以说研读《周易》是孔子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是斤斤计较于孔子是否《易传》之“撰作者”的问题,而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比如喜《易》赞《易》和传《易》的意义上来理解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我们似乎可以说《易传》应该是孔门后学在孔子讲授提纲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整合巫史之易,综合诸子思想完成的一部巨著。
中国社会科学网:孔子对《周易》一书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态度?有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早期和晚期对待《周易》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实际情况怎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杨庆中:孔子是中国易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哲人,按照李学勤先生的观点,孔子是易学的真正开拓者。孔子早年和晚年对《周易》的态度的确实是有一些变化的。孔子“十有五而至于学”,可能很早就对《周易》有所研习,但基本上是从筮占的角度来看待《周易》这本书。帛书《易传》中记有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子贡是孔子55岁去鲁适卫的过程中追随孔子、成为孔子的弟子的,“它日之教”的“它日”当然是在55岁或55岁之后。这说明一直到这个年龄孔子一直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的。其实就是“晚而好《易》”之后孔子也没有改变《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的看法。只不过与以前单纯视《周易》为卜筮之书相比,孔子对《周易》的性质又有了新的认识而已。这也正是帛书《易传》中孔子一再要把自己与巫史做出区别的原因,孔子甚至担心“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
孔子晚年对《周易》的新认识很丰富,言其大者,约有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易》有“古之遗言”。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古之遗言’也不是泛指古代的话,因为《周易》对于孔子来说本来是古代的作品,用不着特别强调。‘遗言’的‘言’应训为教或道,系指前世圣人的遗教。”可见,晚年的孔子,认为《周易》卦爻辞中包含了大量的古圣先贤的遗教。二是强调《易》出于文王,乃忧患之作。今本《易传》和帛书《易传》多次记载孔子的类似言论。如帛书《易传》中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今本《易传》中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由《论语》等典籍可知,孔子对于文王、周公一向崇敬,所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既然孔子推测《周易》出自文王,则其受到孔子的重视,就不难理解了。最后一点是认为《易》为“崇德广业”、“开物成务”之书。“崇德广业”就是高尚其德行,广大其事业。“开物成务”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孔子晚年是把《周易》视为包含了古圣先贤的人道教训,可以成己成物的宝典的。
至于说到孔子早年和晚年对《周易》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可能很多,我能想到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在周游列国时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如《礼记》载孔子的话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据金景芳先生的研究,《坤乾》《夏时》可能就是类似于《周易》的商代、夏代的《易》著。孔子由《坤乾》而知殷道,由《夏时》而知夏道,联想到《周易》,自然会对《周易》有一些新的理解。其次,孔子周游列国时到处碰壁,“急急如丧家之犬”,也迫使他对自己的天命自觉和学思历程有所反思,这也是孔子老而好《易》的主要原因。因此,孔子在其生命的最后五年研读《周易》,手不释卷,并赞《易》传《易》,开出了一条“观其德义”的解《易》新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网:孔子研究《周易》的伟大贡献是什么?
杨庆中:孔子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易学发展的历史,发现在他之前的易说主要表现为巫之易和史之易,巫之易的特点是“赞而不达于数”,史之易的特点是“数而不达于德”。“赞”就是把幽隐的神意显明出来,通俗地讲就是通神。“数”指天地之数。“赞而不达于数”,是说参赞沟通神明(其实就是演绎筮法)但对筮数的本质没有足够的理解,即只知道奇偶之数的吉凶之意,而不知道奇偶之数中包含的天地之道,阴阳之理;“数而不达于德”,是说理解了筮数的本质,但没有透过这一理解进而实现对人道的认识。孔子对他们的观点都不满意,但也没有完全排斥,而是采取了有因有损有益的理性态度,加以整合,提出了“赞而达于数”、“数而达于德”、“仁守而义行之”的易学研究新方向。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易》我观其德义耳也。” 这句话中的“德”就是“数而达于德”之“德”,这句话中的“义”就是“仁守而义行之”之“义”。孔子认为这是他与巫史之《易》“同途而殊归”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德义”就是德行与仁义。就孔子思想的一般意义而言,“德行”与“仁义”,其内涵可以交叉,也可以互相包含。孔子把“德行”与“福”对应,把“仁义”与“吉”对应,在于强调无论是祈求神灵的保佑,还是提高辨识吉凶的能力,都需要回到主体自身,不要向外求。
巫史之《易》,其主要功用是沟通神人或天人,以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寻找上天的旨意、或更为根本的依据,这也正是后来中国哲学核心问题“天人关系”问题的渊薮。孔子并不反对在神人或天人关系的结构中界定人的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孔子正是在此关系结构中来界定人的,这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孔子所反对的是从神的意志(巫)和天道必然性(史)的立场限制人,而主张从人的立场,即从发挥人的能动性的意义上去参赞天地。所以孔子“观其德义”是要把人从一个被规范的对象变成一个可以去参赞宇宙大化的主体。“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亡”即无。无德的人会去频繁地祭祀神灵,缺乏谋略的人会去频繁地占筮。孔子要反其道而行之,让人在自身的德行和智慧上用工夫,即“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不是用卜筮和祭祀的办法,而是从主体的自觉着眼。把人从神的意志(巫之易)和自然(天道)的必然性(史之易)中解放出来,挺立出来,为中国思想的发展开一大格局。我觉得这是孔子对《周易》诠解,乃至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最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网:老子如何看待《周易》,《周易》对老子的思想体系又有何影响?
杨庆中:先秦诸子,彼此的思想之间有联系,又有差异。先哲时贤的相关探讨,比较侧重于讲其“异”,而事实上先秦诸子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知识背景,认同一套共同的知识系统,并在此前提下发表各自的看法。《周易》所彰显的天地人的整体宇宙论就是这一知识系统的核心理念,老子和孔子都是从这一整体宇宙论的观念出发分别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从哲学的意义上讨论“道”的哲学家。老子“道”的哲学的形成,或许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来源,《周易》的卦时-爻位-人的整体宇宙论思想可能也是不可忽视的思想来源之一。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的结果则是从道或天道出发,推演、规范社会政治及人的生命活动的合理性。可以说在天地人的结构里面,老子是站在道或天道的立场来推阐社会人事的,这也正是史之易的特点易经就是中方哲学嘛,这就容易造成重视天道而忽视人道的缺憾。孔子正是为了弥补老子的这一缺憾,而特别强调人道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老子是一位史官,大孔子20来岁,孔子批评史之易,一定意义上可能是针对老子而言的。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网哲学频道编辑李秀伟对杨庆中进行的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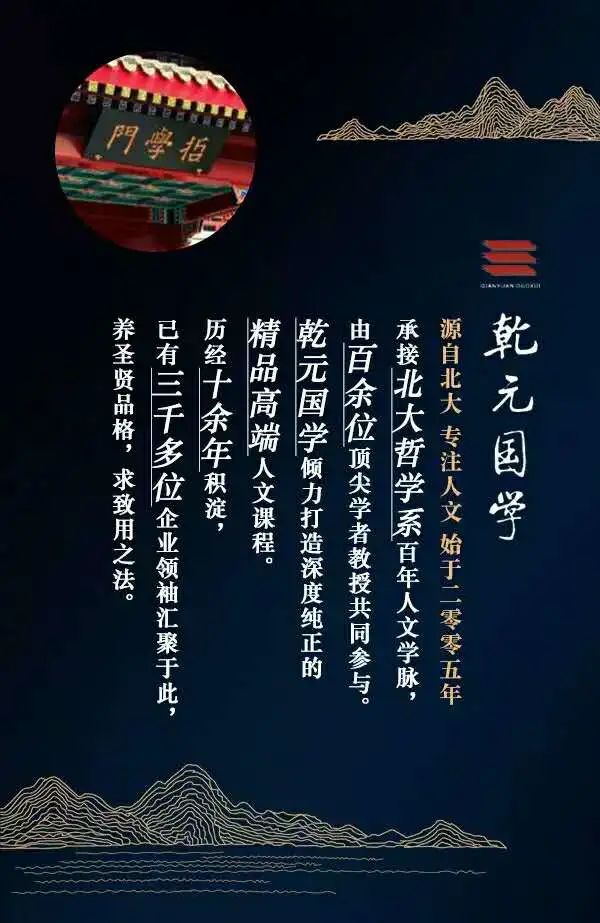
乾元国学
喜欢的话
请转发或点再看
